“生死场”:为“红杏出墙”作辩护(2/3)
文学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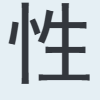 的话语立场问题,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,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。“蒙古包”说,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“点”。但围绕这个“点”的却是无数的“线”和“面”的
的话语立场问题,这是一个太大太泛的题目,根本不适合作博士论文。“蒙古包”说,他只找准其中的某一个“点”。但围绕这个“点”的却是无数的“线”和“面”的 织,甚至“立体”的背景知识,因此,要看的书,作的笔记特别多。
织,甚至“立体”的背景知识,因此,要看的书,作的笔记特别多。
有一回,“蒙古包”在给桂妞的信中谈到萧红的《生死场》,说主 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,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: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“红胡子”被官府杀掉,她要
公王婆在一无所有中升起一种求生的欲望,开始了最原始的反抗:她的亲生儿子因参加“红胡子”被官府杀掉,她要 儿去“报仇”。
儿去“报仇”。
“谁杀死哥哥,你要杀死谁!”——“蒙古包”对这种冤冤相报的传统中国文化有过诸多
 的剖析,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“原谅文化”进行了对比,桂妞觉得很有意思。
的剖析,并将它与西方基督文化中的“原谅文化”进行了对比,桂妞觉得很有意思。
在“蒙古包”极力鼓掇下,桂妞也将《生死场》认真地读了一遍,当她读到一字不识的王婆竟说出了“革命就不怕死……比当 本狗的
本狗的 隶活着强多哪”的话时,桂妞感叹不已。
隶活着强多哪”的话时,桂妞感叹不已。
当时,桂妞觉得王浩对她就像“ 本狗”对“中国
本狗”对“中国 隶”一样,因此,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“不怕死”地去“革命”。
隶”一样,因此,她也应该像王婆那样“不怕死”地去“革命”。
“蒙古包”这种有意无意的鼓励恰恰暗合了桂妞的复杂心理,让她为自己的“红杏出墙”找到了辩护力量。
“手中的灯罩她时刻不能忘记。”鲁迅在给萧红作序时特地说到,“至于老王婆,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,这样的 物,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。”
物,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。”
桂妞想:这样的“灯罩”不但是为了照 ,也是为了自照。照清周围的黑暗,照出自己的灵魂。因此,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“鬼气”呢——“我有什么可怕的?”
,也是为了自照。照清周围的黑暗,照出自己的灵魂。因此,连鲁迅先生都不觉得老王婆有什么“鬼气”呢——“我有什么可怕的?”
特别是桂妞读到在李青山组织举事的宣誓大会上,寡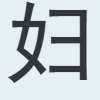 们齐声高呼:“是呀!千刀万剐也愿意!”
们齐声高呼:“是呀!千刀万剐也愿意!”
这声音好像就在桂妞的耳边——这不正是自己那种“ 就
就 吧,疯就疯吧,死就死吧”的激
吧,疯就疯吧,死就死吧”的激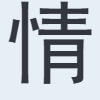 呐喊吗?
呐喊吗?
也许,这正是桂妞的“湖南之行”或“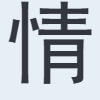 洒湘江”的内在动力?
洒湘江”的内在动力?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